在这个日益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里,系统性的不平等正在发生。无论是零售、金融、物流,还是制造业,人工智能推动的企业都是由一小群高薪员工来管理的,支持这群人的是复杂的自动化技术,以及外围可能数以百万计由算法管理的低收入自由职业者。本文作者认为,当算法管理的劳动力被系统彻底操控,最终他们将面临的就是前途渺茫,晋升无望,工作的两极分化愈发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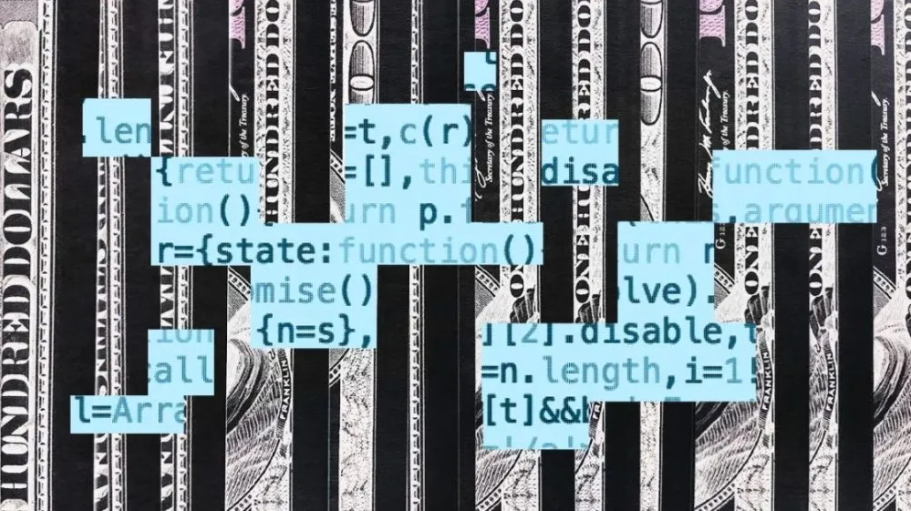
算法歧视与偏见的风险已受到广泛关注和密切审查,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这个日益由人工智能推动的社会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副作用——工作性质本身不断变化所造成的系统性不平等。我们担心未来机器人会夺走我们的工作,可是如果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最终从事的是由算法管理的工作,前途渺茫,晋升无望,又会发生什么?
白手起家取得成功的经典比喻之一是领导者起步卑微,从收发室、收银台或工厂车间一路奋斗向上。虽然做到这一点比好莱坞暗示的要困难许多,但自下而上的升迁至少在传统的企业中是可能的。麦当劳前首席执行官(CEO)查利·贝尔(Charlie Bell)最初是翻烤汉堡的员工。通用汽车董事长兼CEO玛丽·巴拉(Mary Barra)起步于装配线。沃尔玛CEO道格·麦克米伦(Doug McMillon)是从一个配送中心起家的。
相比之下,你认为有多少优步(Uber)司机会有机会获得公司的管理职位,更别提经营这家共享乘车巨头了?有多少未来的亚马逊顶级高管会从送包裹快递或堆码货架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Instacart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及CEO可能亲自交付了公司的第一份订单,可是还有多少人会步其后尘呢?
问题来了:有一个“代码上限”阻止了事业进步——不分性别或种族——因为在人工智能驱动的企业里,初级员工和自由职业者极少与其他人类同事互动。相反,他们是由算法来管理的。
在这个以数字为媒介的工作新时代,通常存在一种层次化的信息流,其中公司会决定他们选择与你分享的信息。不像开出租车那样,司机和调度员之间、司机与司机之间通常有开放的无线电通信,当你为优步或来福车(Lyft)工作时,互动内容是某种优化功能的输出,这种优化功能旨在实现效率和利润最大化。
受算法的管理就会遭到不断的监视与监控。如果你是在中国为美团或饿了么工作的数百万送餐员之一,一种算法就可以确定你应该花多长时间送达一份订单,如果你未能在最后时限前完成,你就会被降薪。同样,亚马逊配送中心的员工也受到算法的密切跟踪;他们必须按“亚马逊步速”工作——有人描述其为“介于行走和慢跑之间的速度”。
当你是一名临时工时,让你担心的不仅仅是你的人工智能老板,你同事通常也是你的竞争对手。比如,住在亚马逊配送点和全食超市(Whole Foods)附近的芝加哥居民称他们看到了智能手机挂在树上的奇怪现象。原因何在?合约快递司机不顾一切要在工作分派上拼赢他们的对手。他们相信,将其设备挂在投递站附近可以帮助他们操纵工作分配算法;置于树上的智能手机可能是比别人早几秒拿到一条15美元送货路线的关键。
过去几十年里,工作一直在不断变化。劳动力市场已日益两极分化,相对于入门级、低技能工作以及要求更高技能水平的高级工作而言,中等技能工作受到了侵蚀。新冠疫情可能加速了这一进程。自1990年以来,美国的每一次衰退之后都是失业型复苏。这一次,随着人工智能、算法和自动化对劳动力队伍的重塑,我们的结局可能更糟糕:K型复苏——那些处于顶端的人前景升腾,而其他每一个人则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财富暴跌。
这种新的数字鸿沟是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领导力指导和工作经验的员工与那些没有机会的人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在我最近的新书《算法领导者》(The Algorithmic Leader)中,我探讨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场景:在为算法工作的大众、拥有设计和训练算法系统的技能和能力的专业特权阶层,以及拥有管理世界的算法平台的少数超级富有贵族之间,存在着阶级鸿沟。
一个全球性的低收入算法劳工队伍已经出现。在拉丁美洲,发展最快的初创企业之一是Rappi,它是Uber Eats、Instacart和TaskRabbit的混合体。波哥大和墨西哥城等城市的客户每单支付1美元左右,或者每月固定支付7美元。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访问一个庞大的按需服务的快递员网络,快递员会将食品、杂货和几乎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送货上门。亚马逊有一个非正式的送货员网络,名为Amazon Flex,随时可以将包裹送到你的家门口——不久之后,甚至可以在大街上把包裹交予你,将包裹放到你的汽车后备箱里,或者打开你的家门,把食品放进你的冰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的演讲《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预言,到2030年左右,生产问题将得到解决,任何东西都足以供应每一个人。然而,问题在于,机器会导致技术性失业。凯恩斯没有完全预料到的情况是,我们目前的高科技就业情况伴随着严重的不平等。
劳动力队伍在变化,工作场所也在变化。你会越来越多地发现,高层管理人员和外围的临时工之间存在差距,甚至在企业内部也是如此。无论是零售还是金融服务,物流还是制造业,人工智能推动的企业都是由一小群高薪员工来管理的,支持这群人的是复杂的自动化技术以及外围可能数以百万计由算法管理的低收入自由职业者。
工作两极分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反馈回路导致的算法不平等陷阱。一旦你成为了依赖智能手机分配任务的零工经济员工,你不仅没有晋升或发展的机会,其他算法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你的处境。请把它想象成为一个数字贫民窟。由于他们的收入和工作任务受市场波动的挟制,这一新的人工智能底层阶级可能会受到自动化系统的不公正对待,这些系统可以决定他们是否有权获得福利、贷款、保险或医疗保健,或者设置剥夺权利的时限。
然而,对一个尚未完全显现的问题寻求快速解决之路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如果这意味着将20世纪的员工保护措施嫁接到21世纪的商业模式上。受民粹主义平台支持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已经在集中精力打击全球数字巨头,力图防止他们逃避纳税义务,努力规范其自由职业队伍的劳动条件,对其数据收集加以限制,甚至对其机器人征税。这些想法中有些是有价值的,另一些尚不成熟,或者更糟糕,只不过是政治秀而已。
算法不平等的长期解决方案不在于税收和监管,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为21世纪提供一个适当的教育体系。重启教育并非易事。真正的问题不是探寻在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而是我们如何教人们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驾驭机器智能,又如何教人们做好终生学习和再培训的准备。
企业领导人要发挥关键作用。他们不仅应该为处于他们企业边缘的自由职业者开拓沟通、反馈和晋升的渠道,而且需要认真对待再培训和社区参与。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正对其一半的员工队伍进行再培训,而思科(Cisco)、IBM、卡特彼勒(Caterpillar)、麦肯锡(McKinsey)和摩根大通(JPMorgan)则在为高中生提供实习机会,并与当地学校合作升级他们的教学课程。这些都是很好的举措,不过还需要更多——不仅是为了社会凝集力,也是为了确保未来劳动力的多元性和灵活性。
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未来计划。如果没有,算法不平等陷阱将不是用统计数字和财富比率来讲述,而是用求救信号来讲述——挂在树上的智能手机、无家可归之人的帐篷城市以及扫描天空并寻找即将终结他们的快递无人机的人类快递员。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物联之家 - 物联观察新视角,国内领先科技门户”,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
延伸阅读
版权所有:物联之家 - 物联观察新视角,国内领先科技门户